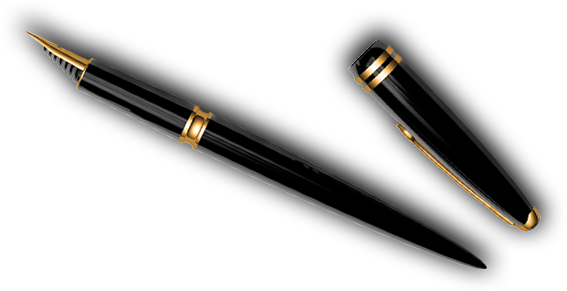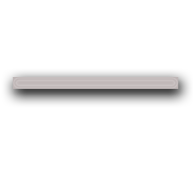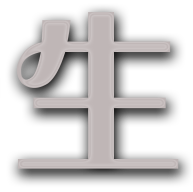爱情的道路 - 2
说来令人难予置信,当年才十几岁的我就已经习惯在安顺、贵阳、镇宁之间到处跑,只要告诉家中人就可以了,甚至有时不告知父母亦不会担心,更何况当时已身在贵阳,不必跟任何人商量,说走就可以走,拿了一个行李箱就跑到三桥搭车,谁知客车已满,本来可以第二天再去的,但生怕回家后受阻或自己会改变主意,当即就选搭上一部往重庆的鱼车,在当时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汽油都久只供军用,民间的交通二工具就只能用酒精或用木炭烧水变成水蒸气去推动机器的汽车,效力当然很差,一来是慢,二是上坡乏力。好不容易行走了三日两夜终于到了重庆南岸,雇了一部滑竿顺长江南岸走了两三个钟头才到角桠她家。这一次轮到我来给她一次大惊喜了,因为她作梦也不会想到以我当时的年纪,会独自一人翻山越岭,经过几天艰辛的路程就是为了见她。她姑父在驻守安顺时同家父及若符大哥都很熟,所以很热情的招待我,当获知我未将此行告知家人时,都说我的不是,并立即拍了一封平安抵达重庆的电报给我父亲。后来的几天都是同她或她的家人聊天,到市区游,看电影,看话剧等。朋友陈振刚,有一晚月光很明,趁大家在田野里摆龙门阵(聊天)时,我同她俩人乘人不觉就走向人迹稀少的地方,坐在田梗上谈天,跟更情不自禁的吻了起来,这是我的初吻,一个难忘的吻,难忘的夜!打后几天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会偷偷地吻。毕竟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太快,转眼学校快要开学,家中亦函电催促,只好怀依依不舍的心情踏上了归途。因为有她姑丈的帮忙,回程就坐了客车。

回安顺没多久,当我正躺在沙发上小休时,突然街上传出了很多爆竹声及小童奔走叫卖「号外」报纸声,并高声欢叫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等不及待跑到街上买了一份,满街的欢叫声加上鞭炮声,令人兴奋莫名,都在分享抗战胜利带来的欢乐,很多人更激动到热泪盈眶,这些年所受战乱及流浪之苦亦将随战的胜利而结束,正所谓苦尽甘来,今后将会有好日子过了。很可惜亦很不幸这种欢欣只不到一年,国共内战由小接触到大规模的打起来。共产党除了正式在战场上同国民党对抗外,更在国民党控制区发动工人及学生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在这样动乱的日子里,我同周守瑛只是断断续续的通讯。记得她给我最后的一封信是由汉口寄到广州海珠南路的,一封好像是在忙中写的短信,在信中没头无脑的希望我能汇一笔数目不小而又说不出用途的钱给她。可能她只知道我家中有钱,但她忘了我当时才二十一岁,只是个向家人伸手要钱而不是管钱的人,我跟本不可能有这么大一笔钱给她,明知道我的回信会令她失望,但我不能不照直说。可能她收到我的信令她不开心,也可能在那个动乱的局势中她根本就没有收到我的回信,从此就断了音讯。
前文说过我因广州公司结束而搬到青年会宿舍居住,与我同房的吴平因职务的需要,经常飞去台湾,在某次他从台北回来时就问我是否认识周守瑛。这一问真令我目瞪舌结,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心想我的天呀!世界是那很大,但在这一刻却显得非常的小了。不是吗?失掉了联系的初恋情人想不到又得知她的下落,莫非这就是所说的命运?上天的安排?当吴平再去台北时,我知道周很爱美,就托他带了些化装品之类的东西给她,她亦托吴平带了一顶台湾手织的草帽给我当回礼,我们又开始了通信。同她重新联系后没有多久我就加入了民航公司,跟共产党的到来,我就跟随公司由广州撤退到香港。后又转做空勤当上了空中服务员。当我得知我将会飞去台北时,心中既兴奋又紧张,因为我将会再见到四五年没有见过面的她,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能再见到故旧已不容易,更何况是初恋的情人!所以那次儿面的过程至今我仍记得非常清楚。我在昏时抵达台北的,洗了澡换了衣服已是华灯初上,急不及待的顾了一辆三轮车直奔她给我的地址。她当时寄居在她姑妈的好朋友唐娘娘家中。那位唐娘娘似乎亦知道我是谁,热情的招呼我进屋子里坐。那是间日式的住宅,房间内全是塌塌米,大家都坐在地上。她很抱歉的说绍斌当晚去参加一个在空军俱乐部的舞会,要夜些才会回来。由于我同唐家不熟,我只好告辞说迟些再来,跟就回到我们飞行员住宿的中国之友俱乐部(Friends of China Club)。它建在总统府对面的新公园内。顾名思义里面住的大部份是外国人,但分了几个大房给中国飞行员住,环境很好,餐厅内中西食物都有而且很可口,虽然我在同几个同事一起吃饭,但没有和他们多作交谈,心中只是在想她,她变成了甚么样一个人,有没有职业,有没有男朋友等,顿时觉得时间过得好慢。饭后在阅览室看了些书报,但只是翻翻而已,那有心思去看,好不容易混到了十点半钟,再乘三轮车前去,但她仍没有回来,这次只好在唐家干等了。谈话中得知那地方除了唐氏夫妇,周守瑛外还有她姑妈的弟弟,弟媳及一个小男孩一起同住。大约快十二时左右听到汽车在门口停下,及男女的欢笑的道到声,没多久,我望的绍斌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雪白的皮肤,爽朗的笑声,逼人的青春,美艳如惜,再加上成长了多几年,更显女性魅力。由于我们久未见面,谈话不知从何开始,但一旦开始了就停不了,不知不觉的就谈到半夜到两点钟左右,才睡在她家客厅里做厅长过了一夜。谈话中得知她亦经历了不少艰辛才到台湾,好容易在台北地方法院找到一份工作,目前的居所只是暂居,稍后会搬到法院的宿舍居住。再谈到姑爹姑妈的一些情,可惜他们一家未能撤退到台湾,我亦告诉他我几年来的情况。
由于我经常港台两边飞,见面的机会亦多了,而每次到台北都是同她在一起,逛街、看电影、跳舞、泡咖啡厅、郊游等。而这段周折了近六年的恋情,在以前只能用通信互诉相思之苦的阶段,亦因这次的见面而成为过去,现在可说是得到了解脱。男未婚女未嫁,又无家长的管束,我们的恋情就像山洪暴发似的一泻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