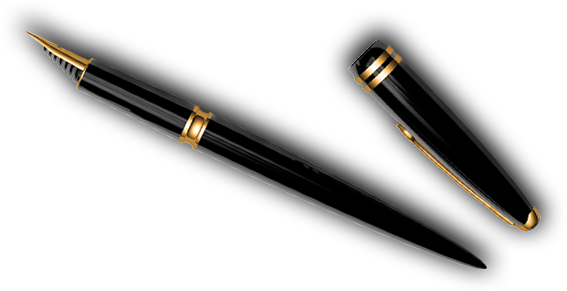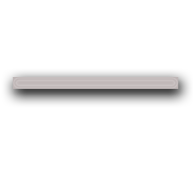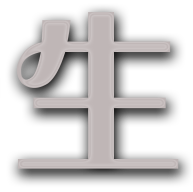回馈祖国 - 1
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大而广泛的题目。我本身是中国人,身上流着的是与祖先一样的血,但我在1984年已移民加拿大,更于1987年成为了加拿大公民,所以得叫中国做祖国了。在我年青的时候,同其他千千万万的青年人一样都是爱国的,希望有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虽然是小资产阶级出生,但抗日战争中所经历及所接触到的众多师生中,不多不少亦受了些左倾的感染,所以对共产党虽说不上崇拜,对他们的理想亦有所认同。在香港及广州读大学时我所办的墙报及歌咏团都用「青火」命名,是一个较前进的名字,在当时国民党的统治下是有一定风险的,我更用了顿河做我写作及画漫画的笔名,它是由一本苏联的名小说《静静的顿河》而来,所以亦算是个「左」的名字。我在美国读航空管理,就是希望他日能为开发中国的交通事业有所贡献。但国内自1950年开始所发生的一切比如三反五反,反右倾,大跃进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等太令人失望,也令人心寒。正所谓亲者痛仇者快,空有一腔报国的热枕,但在那种情况下回国报效,任何人都会有所犹豫的,就这样我就将我最宝贵的中年留在香港为自己创业了。到了1977年国内改革开放后,才能同国内的亲人取得联系。在我三个亲兄长中只有廷琨二哥夫妇及伯符大嫂尚在,众多的堂兄长中亦祇有三房的邓迁三哥在广州,廷璞五哥在贵阳,四房廷法二哥夫妇在天津。当我们约了在广州见面时的那一刻,真如劫后重生,再次见面,所见所听的一切都令人心酸及心痛,而他们的经历及所受的苦难不是用短短的语言可以描述,国内的贫困落后更是难以令人置信。廷琨二哥大概是受了政府的委托,或是他一厢情愿,好几次企图游说我到国内投资,但我都没有表示,最主要是我这一生从事的运输业务是服务性的行业,我们并不拥有飞机或货船,我们祇是做这些公司的代理,从中收取差价或代理佣金。我们做所谓的「代理」;当时在国内连听都没听过,因为国内的运输全是国营,对「代理」没那种需要,至于从事其他行业吧,我同我的三个儿子从未做过贸易,更未涉足过实业,亦感无从入手,我只好跟随中国的至理名言「不熟不做」,放弃了如大家说的发大财,或说得好听一点,効劳祖国的机会。但在内心里我并没有忘记要为国家做点甚么。
我知道国内一部分亲人对我可能有竟见,因为我毕竟是邓家唯一在国外事业有成之人,我应该为祖国的开发尽力,一方面能光宗耀祖,另方面亦可使国内亲友们面上有光,或因此而有所获,我其实又何尝不想呢,但现实却不是那末简单。

首先我的资金是经我五十年的辛勤工作一点一滴凑起来的血汗钱,由于我个性保守,在投资方面只求隐健,不求暴利,我也知道国内市场无比的大,赚钱的会很多,但两个人为的因素令我却步;第一是国内的官僚主义太重,关卡重重,令人难以应付,需花时间去磨,去应付,我没有时间亦不习惯。第二是贪污盛行,要跟随这股歪风,就会加重经营的成本,这且不说,如弄得不好后果可就严重了。想想我一介商人,几十年来奉公守法,赚钱虽不多,但心安理得,况且已近退休之年,何必再去做一些自己不熟习兼且不愿意的投资呢?所以就算有一些很好的提议,我都没有心动。只是在默想美国已故肯尼地总统向青年人讲过的两句演词:「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甚么,问问你能为国家做些甚么。」我既然没有本事去赚国家的钱,或为国家去赚钱,我想我总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花点钱来回馈祖国吧!这个问题在我心中孕育了好几年,一直到1999年才让我想到了在香港成立一个「邓廷琮教育基金会」,拨一笔款项做基金,将其生的利息及投资得来的利润用在国内的教育事业上。我认为中国以长远来说最需要的是办好教育;普及的及专业的,这才是国之本,国之基,尤其是我见到了我的子侄辈及千千万万的其他青年,在他们一生最宝贵、最需要读书及学习的年华都荒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教育的断层不知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得以弥补,真个令人痛心。
这个基金会终于在2000年四月十九日在香港注册成立,并由一个董事局负责管理、审核及监督款项的应用,成员是我及三个儿子。基金会的主要工作着重在贵州,有见于我们董事会成员对国内的一切既不熟习亦欠了解,也不可能经常回去走动联络,必需有一个国内的人参予,以补我们的不足,就聘请了当时贵州省政府在港窗口机构贵达公司总经理杨德林先生担任基金会顾问,经我向他解说基金会的成立及目的后,他极表赞同,他说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并表明一定尽全力帮忙同国内构通,将此事尽早落实。

在他的安排下,我及友杰带同三个儿子终于在2000年的三月三十一日踏足到我幼年及少年成长的故乡,见到很多半个世纪没有见过面的亲人、朋友及同学。由于是首次回乡,加上杨德林顾问的安排,省市级的政府、政协、统战部、海外联谊会及侨联侨办等的领导都接见并设宴欵待。我在政协主席的欢迎会上同时宣布了「邓廷琮教育基金会」的成立并要求政府帮助将此事落实,很高兴实时得到主席的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