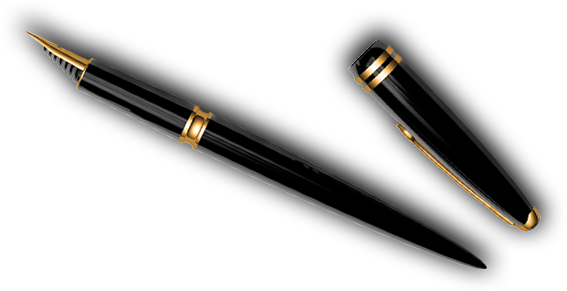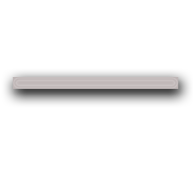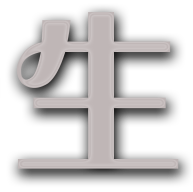我的成長 - 1
我是1926年農曆四月二十八日在雲南昆明出世, 所以乳名(小名)就叫昆明。由於當時身旁沒有鐘或錶,不知出世的準確時間,但母親記得當我離開母體後就聽到雞叫,俗語說「雞鳴丑時」所以就當我在丑時出世。我才幾個月大,就舉家由昆明搬回貴州安順定居,當時尚未有公路。交通工具就是騎馬、坐轎、坐滑竿或是走路,高山峻嶺旅途甚為艱險。據母親說上路幾天後我就發高燒,到投宿客棧呼吸差不多已停頓,有人建議放棄治療就當我已死算了,但母親卻抱我堅持不放,並堅持必須「死馬當活馬」來醫。結果找來了一個鄉下土郎中煎了付藥,但我牙關咬緊,咀巴張不開,無法喂藥。最後決定用燒艾的土法將一種點燃了的草藥「艾」放在咀巴兩邊去刺激神經令咀巴張開,這才能將藥灌進咀。也許是我命不該絕,第二天開始有一點起色,大隊就決定在那裡停多幾天以便調理。雖然現在我的咀巴兩邊仍留下燒過的痕跡,但因此而能活下來是一萬個值得的,亦正如母親所說我的命是檢回來的。
很難說我們家是否富有,正如一般所說「強中自有強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不過以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安順來說,可說是上等人家了。在西街的護法路(又名圍牆背後)有一間兩層樓的住房,四面都是高高的石牆,大門向西開,先要上四級石階才到十尺寬的大門,最上一級石階兩旁有兩張石櫈。裏面分前後院,圍着前院四面的是兩層高的樓房,而在第二層樓的房與房之間的前面都有騎樓相連,俗稱「走馬騎樓」,對大門的樓房叫正廳,而對面的樓房就叫對廳,兩旁就叫廂房,前院亦算大,可供我們學騎自行車、滾鐵環,過年時還可舞龍。由於父親同二伯父合夥做生意,所以就同住這間大屋。一進大門右面是我們家,左面是二伯父家,後院是花園,種有桃樹及臘梅,還有個金魚缸,花園兩旁是廚房,殼倉及廁所。
在當時的農村社會賺到錢就是買田買地買房子,我們家亦不例外。房產方面除了上述住房外,在雙眼井有一個四合院的房子,大十字南街口有一間三層樓高前後居的商業大樓 (我們全家在2000年首次回鄉掃墓時曾去拍下照片,之後由於市區重建,就被拆掉)。另在西門外有一間兩層樓的中型旅館。至於田產方面我不知有多少畝田或多少畝地,祗知是租給苗族耕種,每年收成後,他們會擔一部份殼物來當租金,並手抱幾隻自養雞當禮物送來家中,母親亦回送一個裝有現金的紅封以示謝意而皆大歡喜。國內在過往幾十年經過了不少大小運動、鬥爭、清算,這所有的一切都不再是我們的了。
由於沒有自來水,每戶人家都要將買來一桶一桶的井水儲進一個大水缸備用,普通人家多用瓦缸,只有小數人家才會用石缸,那是將一塊幾百斤重的大石,將中間鑿空而成的,當然這就很貴,除了是一種身份象徵外,在實用上來說可以用到子孫輩,而我們家用的是更高一級的半圓形石缸。厠所俗稱毛坑。共有四個,前院及後院左右角各有一個,農民會出錢買糞便當肥料去施菜。家中有一個表姐幫母親當家,並有三個丫環名春來、夏喜及冬梅。大哥及二哥都在上海,三哥在廣西梧州,家中男丁就祇有父親和我,我那時可說是在女人堆中成長的,這是否影響我後來常喜同女人在一起,及學京戲選唱青衣有關那就不知道了。母親經常忙於準備家中必需的食物,如泡菜、糟辣椒等,過年前更忙得不亦樂乎,要自己製造血荳腐、香腸、臘肉、高粑等。她經常亦到隔壁大府公園軍營裡同師長太太們打麻將,師長名猶國才,娶了四五個太太而每一個太太都用出生地名來區分,比如貴陽太,定南太,洪江太等。他有部小驕車每次出車都有兩個馬弁(即現在的侍衛)站在車旁的踏板上以便保護並開關車門。我曾同母親坐過幾次,好不威風。
大概到六歲才開始讀小學,祇記得當時還得勞動家中數人又抱又抬的把我送進了在家斜對面的第一男小,校長名趙裕宗。也許是性格使然,一旦入學後我就變得很活躍。參加幼童軍,接受了既健康,有趣味而又實用的訓練,又是學校樂隊的小鼓鼓手,每次出街遊行或有慶典時能做鼓手而走在前面令我感到自豪。在運動會上我參加了單槓雙槓比賽,雖得不到獎,但有滿足感。我亦有參加演講比賽,不記得是否拿過獎,大概沒有吧。
廷琪三哥與我相差八歲,但我們沒有感受到那種年齡差距,而且感情還特別好,他很愛惜我也很關懷我。在梧州上培正中學時就經常寄一些兒童讀物給我,讓我自小就有機會認識史可法、司馬光、岳飛、文天祥、愛迪生、牛頓、拿破崙等中外歷史人物。到上海讀復旦大學後又為我訂了科學畫刋,使我對當時舊金山的金門大橋,取名「中國飛剪」號的水陸兩用越洋飛機。世界最大法國郵輪「諾曼地」號等有所認識,因此而讓同學們羨慕不已。由於經常有人來回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家中常有時興的衣物及用品,亦有上等糖果餅乾供享用。雖有父母的疼惜,兄長的愛護,親友的奉承,丫環們的侍候,但我並沒有因此而被寵壞;吃飯不挑食,穿着無所謂,不發少爺脾氣亦不擺架子。大概我是所謂的「少年老成」吧,幫家中做生意的員工們都叫我「老機器」。又因為我自幼常生病而身型很瘦,同學們都叫我「牛肉乾」。

中學第一年是在父親曾捐助「羲之圖書館」大樓的全男生縣立安順中學,記得當英文課的外省藉老師讀到字母B 時,大家祇是笑而不讀,因為貴州話這個字母同女人私處是同樣的發音,真令人發噱。一年後轉讀普定縣私立建國中學,普定距離安順大約四五十公里,坐滑竿要一天路程,我忘了當時為甚麼要轉學。可能是因為那是父親有份參與新建的學校,同時校長亦是父親朋友兒子名丁達三在上海大學畢業後滿懷抱負回來主辦的,心想那將會是間好學校,所以就同若符大哥的大兒子承文一起前去就讀,但很不幸他才讀了幾個月就得急症過世了。
在建國中讀了一個學期就回安順讀一間新辦的黔江中學,原因有三,(一)是普定畢竟離安順稍遠,經常兩頭跑不很方便,(二)是承文過身後少了個伴,(三)是中英庚款董事會在安順創辦的黔江中學是間較特別的學校。雖然稍後附件我會有專文介紹,但我仍得在此提上一筆,因為這間學校對我後來的影響很大:(一)經費充足,師資及設施在當時可說是數一數二的,因此可能接受到較好的教育,(二)學校雖在東門外幾里路離家不遠的金鐘山腳下,必需同其他同學一樣要住讀,因此培養了我獨主及合群的性格,(三)正值抗日戰爭,同學多是來自全國各地,加上省內的少數民族使我對國內其他地區及省內少數民族有所認識,(四)同學中不少是戰爭中的孤兒,我因而對貧困、孤獨、無靠的人有更深的瞭解,並寄予同情。一段多令人難忘的歲月。
在學五年中我是個很活躍的學生,參加歌詠團、唱京戲及演話劇。話劇有《野玫瑰》、《家》、《雷雨》。而《北京人》亦曾排練了很久,但可惜沒有演出。京戲我曾演過《蘇三起解》的蘇三及《華容道》的關公。記得我扮關公一出場,我的好朋友(香港人所說的死黨)坐在台下第一排的朱亦蘭大聲說,「怎關公的臉那麼小!」立即引起了哄堂大笑,我同台上的幾個演員亦忍不住的都笑了,只因我人很瘦,小瞼上戴上頭盔,再加下面的鬍子,塗上紅包的面部的確所剩無幾了。這是段令人難忘的歲月,雖然物質生活很苦但精神生活卻非常充實,而且大家只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打敗日本鬼子,重拾舊山河,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
再回到家庭方面,在1937年四月廷琪三哥在安順渡完春假準備回上海,得到開明的父母的同意後我就跟隨三哥一起去上海準備讀小學。一個十一歲大的孩子到了那個十里洋場的上海真如紅樓夢中的劉佬佬進了大觀園,一切都是那麼新鮮有趣。抽水馬桶、冰淇琳、自動電樓梯等等。學校已經安排好就讀天主教辨的曉星小學,只等秋季開學。誰知日本人於七月七日在北京附近永定河邊挑起了盧溝橋事故而同國軍打了起來。在那個年代中日間的大小事故是常有的事,一般很少會認真看待。但這次可不同了,因為政府揚言要同日本人拼到底,所以大家意識到這將將會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戰,可能會是一場持久戰。經家人商量後就決定,除了伯符大哥必須留在上海處理公司的業務外,舉家都回鄉避戰。由於廷琨二哥仍在湖南長沙未婚妻家渡暑假,這個搬遷的擔子就放在才二十歲廷琪三哥及十二歲我的肩上。伯符大嫂帶同五個小孩及很多行李,經過了半個月艱辛的旅程,終於回到了安順老家。這場戰不袛是將我在上海讀書的美夢打破,亦將中國弄得個天翻地覆。
中日戰爭整整打了八年,這八年我在戰爭中渡過,亦在戰爭中成長。大哥廷瑄(伯符)在結束了上海的生意後也回到安順,定居大用鄉,在那的半山上他修建了一座洋房打算長住。印象中因為當時沒有甚麼生意可做,他只是每天練練字,讀些書。二哥廷琨亦由長沙未婚妻那裡回到了安順同家人商議何去何從。當時他已在上海法國天主教辦的震旦大學讀了三年醫科,問題是他是否再回上海或改到法國巴黎繼續求學。最後決定還是回上海繼續學業。照當時的情況來看,雖然日本已佔領了上海,但住在租界裡還是安全的,反而因德國的希特拉不斷在製造事端,歐洲的局勢更不穩定。他先到昆南,再乘火車南下到法屬安南(現在的越南)的海防市,轉乘法國郵輪赴上海。回到上海沒有多久他就同童恩信結了婚。二嫂是世代書香人家出身,曾祖父曾中過狀元,她彈得一手好鋼琴。廷琨二哥在上海時也有學小提琴,因此在安順家中的一次聚會中,曾應大家的要求拉小提琴給家人及在坐的朋友欣賞,評語是這西洋的東西沒有二胡那末好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