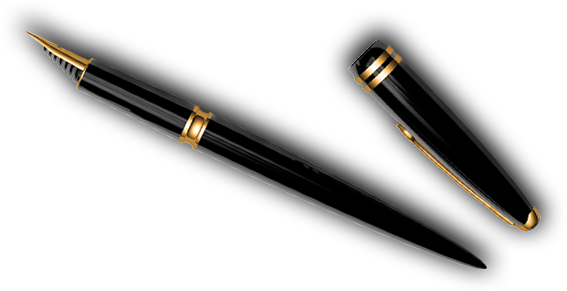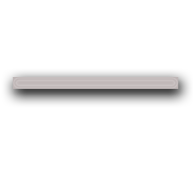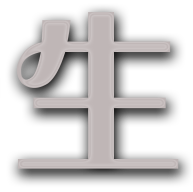回饋祖國 - 1
現在讓我來說說這個大而廣泛的題目。我本身是中國人,身上流着的是與祖先一樣的血,但我在1984年已移民加拿大,更於1987年成為了加拿大公民,所以得叫中國做祖國了。在我年青的時候,同其他千千萬萬的青年人一樣都是愛國的,希望有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中國,雖然是小資產階級出生,但抗日戰爭中所經歷及所接觸到的眾多師生中,不多不少亦受了些左傾的感染,所以對共產黨雖說不上崇拜,對他們的理想亦有所認同。在香港及廣州讀大學時我所辦的壁報及歌詠團都用「青火」命名,是一個較前進的名字,在當時國民黨的統治下是有一定風險的,我更用了頓河做我寫作及畫漫畫的筆名,它是由一本蘇聯的名小說《靜靜的頓河》而來,所以亦算是個「左」的名字。我在美國讀航空管理,就是希望他日能為開發中國的交通事業有所貢獻。但國內自1950年開始所發生的一切比如三反五反,反右傾,大躍進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等等太令人失望,也令人心寒。正所謂親者痛仇者快,空有一腔報國的熱枕,但在那種情況下回國報效,任何人都會有所猶豫的,就這樣我就將我最寶貴的中年留在香港為自己創業了。到了1977年國內改革開放後,才能同國內的親人取得聯繫。在我三個親兄長中只有廷琨二哥夫婦及伯符大嫂尚在,眾多的堂兄長中亦祇有三房的鄧遷三哥在廣州,廷璞五哥在貴陽,四房廷法二哥夫婦在天津。當我們約了在廣州見面時的那一刻,真如劫後重生,再次見面,所見所聽的一切都令人心酸及心痛,而他們的經歷及所受的苦難不是用短短的語言可以描述,國內的貧困落後更是難以令人置信。廷琨二哥大概是受了政府的委託,或是他一廂情願,好幾次企圖遊說我到國內投資,但我都沒有表示,最主要是我這一生從事的運輸業務是服務性的行業,我們並不擁有飛機或貨船,我們祇是做這些公司的代理,從中收取差價或代理佣金。我們做所謂的「代理」;當時在國內連聽都沒聽過,因為國內的運輸全是國營,對「代理」沒那種需要,至於從事其他行業吧,我同我的三個兒子從未做過貿易,更未涉足過實業,亦感無從入手,我只好跟隨中國的至理名言「不熟不做」,放棄了如大家說的發大財,或說得好聽一點,効勞祖國的機會。但在內心裡我並沒有忘記要為國家做點甚麼。
我知道國內一部分親人對我可能有竟見,因為我畢竟是鄧家唯一在國外事業有成之人,我應該為祖國的開發盡力,一方面能光宗耀祖,另方面亦可使國內親友們面上有光,或因此而有所獲,我其實又何嘗不想呢,但現實卻不是那末簡單。

首先我的資金是經我五十年的辛勤工作一點一滴湊起來的血汗錢,由於我個性保守,在投資方面只求隱健,不求暴利,我也知道國內市場無比的大,賺錢的會很多,但兩個人為的因素令我卻步;第一是國內的官僚主義太重,關卡重重,令人難以應付,需花時間去磨,去應付,我沒有時間亦不習慣。第二是貪汚盛行,要跟随這股歪風,就會加重經營的成本,這且不說,如弄得不好後果可就嚴重了。想想我一介商人,幾十年來奉公守法,賺錢雖不多,但心安理得,況且已近退休之年,何必再去做一些自己不熟習兼且不願意的投資呢?所以就算有一些很好的提議,我都沒有心動。只是在默想美國已故肯尼地總統向青年人講過的兩句演詞:「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甚麼,問問你能為國家做些甚麼。」我既然沒有本事去賺國家的錢,或為國家去賺錢,我想我總可以在我的能力範圍內花點錢來回饋祖國吧!這個問題在我心中孕育了好幾年,一直到1999年才讓我想到了在香港成立一個「鄧廷琮教育基金會」,撥一筆款項做基金,將其生的利息及投資得來的利潤用在國內的教育事業上。我認為中國以長遠來說最需要的是辦好教育;普及的及專業的,這才是國之本,國之基,尤其是我見到了我的子姪輩及千千萬萬的其他青年,在他們一生最寶貴、最需要讀書及學習的年華都荒廢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這個教育的斷層不知要經過多少年才能得以彌補,真個令人痛心。
這個基金會終於在2000年四月十九日在香港註冊成立,並由一個董事局負責管理、審核及監督款項的應用,成員是我及三個兒子。基金會的主要工作着重在貴州,有見於我們董事會成員對國內的一切既不熟習亦欠了解,也不可能經常回去走動聯絡,必需有一個國內的人參予,以補我們的不足,就聘請了當時貴州省政府在港窗口機構貴達公司總經理楊德林先生担任基金會顧問,經我向他解說基金會的成立及目的後,他極表贊同,他說這是「利在當代,功在千秋」,並表明一定盡全力幫忙同國內構通,將此事盡早落實。

在他的安排下,我及友傑帶同三個兒子終於在2000年的三月三十一日踏足到我幼年及少年成長的故鄉,見到很多半個世紀沒有見過面的親人、朋友及同學。由於是首次回鄉,加上楊德林顧問的安排,省市級的政府、政協、統戰部、海外聯誼會及僑聯僑辦等的領導都接見並設宴欵待。我在政協主席的歡迎會上同時宣佈了「鄧廷琮教育基金會」的成立並要求政府幫助將此事落實,很高興即時得到主席的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