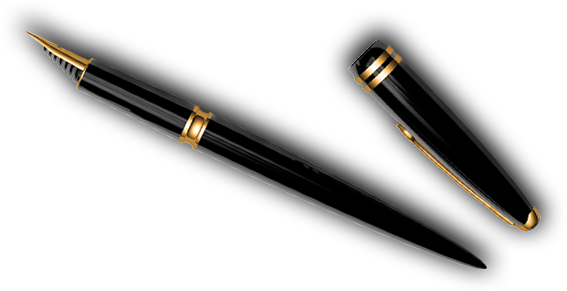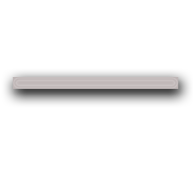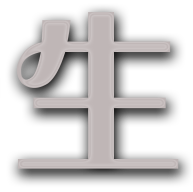我的成长 - 1
我是1926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在云南昆明出世, 所以乳名(小名)就叫昆明。由于当时身旁没有钟或表,不知出世的准确时间,但母亲记得当我离开母体后就听到鸡叫,俗语说「鸡鸣丑时」所以就当我在丑时出世。我才几个月大,就举家由昆明搬回贵州安顺定居,当时尚未有公路。交通工具就是骑马、坐轿、坐滑竿或是走路,高山峻岭旅途甚为艰险。据母亲说上路几天后我就发高烧,到投宿客栈呼吸差不多已停顿,有人建议放弃治疗就当我已死算了,但母亲却抱我坚持不放,并坚持必须「死马当活马」来医。结果找来了一个乡下土郎中煎了付药,但我牙关咬紧,咀巴张不开,无法喂药。最后决定用烧艾的土法将一种点燃了的草药「艾」放在咀巴两边去刺激神经令咀巴张开,这才能将药灌进咀。也许是我命不该绝,第二天开始有一点起色,大队就决定在那里停多几天以便调理。虽然现在我的咀巴两边仍留下烧过的痕迹,但因此而能活下来是一万个值得的,亦正如母亲所说我的命是检回来的。
很难说我们家是否富有,正如一般所说「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不过以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安顺来说,可说是上等人家了。在西街的护法路(又名围墙背后)有一间两层楼的住房,四面都是高高的石墙,大门向西开,先要上四级石阶才到十尺宽的大门,最上一级石阶两旁有两张石櫈。里面分前后院,围着前院四面的是两层高的楼房,而在第二层楼的房与房之间的前面都有骑楼相连,俗称「走马骑楼」,对大门的楼房叫正厅,而对面的楼房就叫对厅,两旁就叫厢房,前院亦算大,可供我们学骑自行车、滚铁环,过年时还可舞龙。由于父亲同二伯父合伙做生意,所以就同住这间大屋。一进大门右面是我们家,左面是二伯父家,后院是花园,种有桃树及腊梅,还有个金鱼缸,花园两旁是厨房,壳仓及厕所。
在当时的农村社会赚到钱就是买田买地买房子,我们家亦不例外。房产方面除了上述住房外,在双眼井有一个四合院的房子,大十字南街口有一间三层楼高前后居的商业大楼 (我们全家在2000年首次回乡扫墓时曾去拍下照片,之后由于市区重建,就被拆掉)。另在西门外有一间两层楼的中型旅馆。至于田产方面我不知有多少亩田或多少亩地,祗知是租给苗族耕种,每年收成后,他们会担一部份壳物来当租金,并手抱几只自养鸡当礼物送来家中,母亲亦回送一个装有现金的红封以示谢意而皆大欢喜。国内在过往几十年经过了不少大小运动、斗争、清算,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再是我们的了。
由于没有自来水,每户人家都要将买来一桶一桶的井水储进一个大水缸备用,普通人家多用瓦缸,只有小数人家才会用石缸,那是将一块几百斤重的大石,将中间凿空而成的,当然这就很贵,除了是一种身份象征外,在实用上来说可以用到子孙辈,而我们家用的是更高一级的半圆形石缸。厕所俗称毛坑。共有四个,前院及后院左右角各有一个,农民会出钱买粪便当肥料去施菜。家中有一个表姐帮母亲当家,并有三个丫环名春来、夏喜及冬梅。大哥及二哥都在上海,三哥在广西梧州,家中男丁就祇有父亲和我,我那时可说是在女人堆中成长的,这是否影响我后来常喜同女人在一起,及学京戏选唱青衣有关那就不知道了。母亲经常忙于准备家中必需的食物,如泡菜、糟辣椒等,过年前更忙得不亦乐乎,要自己制造血荳腐、香肠、腊肉、高粑等。她经常亦到隔壁大府公园军营里同师长太太们打麻将,师长名犹国才,娶了四五个太太而每一个太太都用出生地名来区分,比如贵阳太,定南太,洪江太等。他有部小骄车每次出车都有两个马弁(即现在的侍卫)站在车旁的踏板上以便保护并开关车门。我曾同母亲坐过几次,好不威风。
大概到六岁才开始读小学,祇记得当时还得劳动家中数人又抱又抬的把我送进了在家斜对面的第一男小,校长名赵裕宗。也许是性格使然,一旦入学后我就变得很活跃。参加幼童军,接受了既健康,有趣味而又实用的训练,又是学校乐队的小鼓鼓手,每次出街游行或有庆典时能做鼓手而走在前面令我感到自豪。在运动会上我参加了单杠双杠比赛,虽得不到奖,但有满足感。我亦有参加演讲比赛,不记得是否拿过奖,大概没有吧。
廷琪三哥与我相差八岁,但我们没有感受到那种年龄差距,而且感情还特别好,他很爱惜我也很关怀我。在梧州上培正中学时就经常寄一些儿童读物给我,让我自小就有机会认识史可法、司马光、岳飞、文天祥、爱迪生、牛顿、拿破仑等中外历史人物。到上海读复旦大学后又为我订了科学画刋,使我对当时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取名「中国飞剪」号的水陆两用越洋飞机。世界最大法国邮轮「诺曼底」号等有所认识,因此而让同学们羡慕不已。由于经常有人来回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家中常有时兴的衣物及用品,亦有上等糖果饼干供享用。虽有父母的疼惜,兄长的爱护,亲友的奉承,丫环们的侍候,但我并没有因此而被宠坏;吃饭不挑食,穿着无所谓,不发少爷脾气亦不摆架子。大概我是所谓的「少年老成」吧,帮家中做生意的员工们都叫我「老机器」。又因为我自幼常生病而身型很瘦,同学们都叫我「牛肉干」。

中学第一年是在父亲曾捐助「羲之图书馆」大楼的全男生县立安顺中学,记得当英文课的外省藉老师读到字母B 时,大家祇是笑而不读,因为贵州话这个字母同女人私处是同样的发音,真令人发噱。一年后转读普定县私立建国中学,普定距离安顺大约四五十公里,坐滑竿要一天路程,我忘了当时为甚么要转学。可能是因为那是父亲有份参与新建的学校,同时校长亦是父亲朋友儿子名丁达三在上海大学毕业后满怀抱负回来主办的,心想那将会是间好学校,所以就同若符大哥的大儿子承文一起前去就读,但很不幸他才读了几个月就得急症过世了。
在建国中读了一个学期就回安顺读一间新办的黔江中学,原因有三,(一)是普定毕竟离安顺稍远,经常两头跑不很方便,(二)是承文过身后少了个伴,(三)是中英庚款董事会在安顺创办的黔江中学是间较特别的学校。虽然稍后附件我会有专文介绍,但我仍得在此提上一笔,因为这间学校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一)经费充足,师资及设施在当时可说是数一数二的,因此可能接受到较好的教育,(二)学校虽在东门外几里路离家不远的金钟山脚下,必需同其他同学一样要住读,因此培养了我独主及合群的性格,(三)正值抗日战争,同学多是来自全国各地,加上省内的少数民族使我对国内其他地区及省内少数民族有所认识,(四)同学中不少是战争中的孤儿,我因而对贫困、孤独、无靠的人有更深的了解,并寄予同情。一段多令人难忘的岁月。
在学五年中我是个很活跃的学生,参加歌咏团、唱京戏及演话剧。话剧有《野玫瑰》、《家》、《雷雨》。而《北京人》亦曾排练了很久,但可惜没有演出。京戏我曾演过《苏三起解》的苏三及《华容道》的关公。记得我扮关公一出场,我的好朋友(香港人所说的死党)坐在台下第一排的朱亦兰大声说,「怎关公的脸那么小!」立即引起了哄堂大笑,我同台上的几个演员亦忍不住的都笑了,只因我人很瘦,小睑上戴上头盔,再加下面的胡子,涂上红包的面部的确所剩无几了。这是段令人难忘的岁月,虽然物质生活很苦但精神生活却非常充实,而且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打败日本鬼子,重拾旧山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
再回到家庭方面,在1937年四月廷琪三哥在安顺渡完春假准备回上海,得到开明的父母的同意后我就跟随三哥一起去上海准备读小学。一个十一岁大的孩子到了那个十里洋场的上海真如红楼梦中的刘佬佬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抽水马桶、冰淇琳、自动电楼梯等等。学校已经安排好就读天主教辨的晓星小学,只等秋季开学。谁知日本人于七月七日在北京附近永定河边挑起了卢沟桥事故而同国军打了起来。在那个年代中日间的大小事故是常有的事,一般很少会认真看待。但这次可不同了,因为政府扬言要同日本人拼到底,所以大家意识到这将将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可能会是一场持久战。经家人商量后就决定,除了伯符大哥必须留在上海处理公司的业务外,举家都回乡避战。由于廷琨二哥仍在湖南长沙未婚妻家渡暑假,这个搬迁的担子就放在才二十岁廷琪三哥及十二岁我的肩上。伯符大嫂带同五个小孩及很多行李,经过了半个月艰辛的旅程,终于回到了安顺老家。这场战不袛是将我在上海读书的美梦打破,亦将中国弄得个天翻地覆。
中日战争整整打了八年,这八年我在战争中渡过,亦在战争中成长。大哥廷瑄(伯符)在结束了上海的生意后也回到安顺,定居大用乡,在那的半山上他修建了一座洋房打算长住。印象中因为当时没有甚么生意可做,他只是每天练练字,读些书。二哥廷琨亦由长沙未婚妻那里回到了安顺同家人商议何去何从。当时他已在上海法国天主教办的震旦大学读了三年医科,问题是他是否再回上海或改到法国巴黎继续求学。最后决定还是回上海继续学业。照当时的情况来看,虽然日本已占领了上海,但住在租界里还是安全的,反而因德国的希特拉不断在制造事端,欧洲的局势更不稳定。他先到昆南,再乘火车南下到法属安南(现在的越南)的海防市,转乘法国邮轮赴上海。回到上海没有多久他就同童恩信结了婚。二嫂是世代书香人家出身,曾祖父曾中过状元,她弹得一手好钢琴。廷琨二哥在上海时也有学小提琴,因此在安顺家中的一次聚会中,曾应大家的要求拉小提琴给家人及在坐的朋友欣赏,评语是这西洋的东西没有二胡那末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