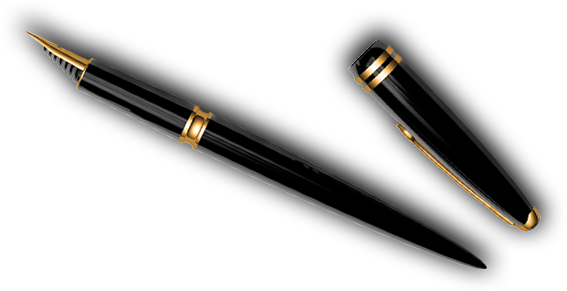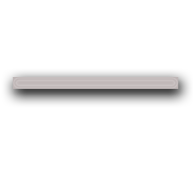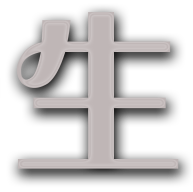我的成长 - 2
虽然上海给日本占领但英法租界仍是安全区,汇钱并不困难,直到日本同英美开战将英美法租界占领后,汇钱才成了问题,母亲为此事担心不已,但父亲叫母亲不用操心,他认为廷琨自会有办法解决的。父亲果然说对了,据后来廷琨二哥说当时他是靠买卖二手照相机维生的,不只赚到钱并对相机有更深认识,而且对摄影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滬期间他还继续追随一个俄国音乐家学习小提琴。我们可以想象新婚的廷琨拉小提琴而恩信用钢琴伴奏,正所谓夫唱妇随其乐也融融,多么的罗曼蒂克,这亦可将当时的恶劣环境冲淡些吧。
廷琪三哥考取了贵州省立工学院的土木工程系后,就继续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未完成的学业。学校是贵阳南郊十几公里的图关,我有时趁周末由安顺跑去看他而他亦常回安顺。正如前文所说虽然我们年龄有差距,但相处得非常好,常常睡在一张床上交谈到半夜。他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人聪明,手更巧。能将他的一条西装裤改成一件夹克给我穿,自己冲洗照片,用铅水在自制的模子里制造鸟枪所用比火柴头大一点的子弹。能为京剧或话剧的演员化装,拉京胡,拉锯琴,吹口琴,唱京戏,演话剧所谓无所不能,我对他是既崇拜又敬爱。在贵阳有一次我们同睡一床,听到他半夜辛苦的咳嗽声,令我感到难过及心痛,我求天主让我代他病,代他咳嗽,别让他那么辛苦。在他想娶秀珍为妻时为父亲反对,一来她母亲是个寡妇,那就表示命不好,二来她家开的是棺材铺,是一种厌恶性及不吉利的行业。三哥为此非常不开心,把自己关在楼上的睡房中两天不下楼吃饭,我却紧张得不得了,担心他生病,又怕他会自杀,除了每天几次在他睡房门口张望,又向天主祈祷,保佑三哥不要因此而生病,并能完成心愿,母亲亦从旁开解父亲。由于三哥的果断行动,让父亲看出了他的决心,加上母亲及亲友的说项,父亲终于应允了这件婚事,至于我的祈祷是否有助,那就不得而知了。但他们终于结了婚,而当时在安顺还是一件大事呢!
在黔江中学读书时有两件令人难忘的事值得在此一提:某一个暑假前夕在举行了散学晚会后大约九点左右,我同朱亦兰、詹宝瑜决定当晚不留在学校而回安顺县城。漆黑的夜空到处鳞火闪闪,虫声阁阁,我们沿公路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抵达了已关闭的城门,我们便喊城说是学生,但守城的军人说甚么都不肯开城门。如果再回学校又得再走一个钟头,而大家都很疲倦,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朱亦兰记起在离城门两百码左右,有一处倒塌的城墙,我们决定就从那里神不知鬼不觉的爬上去。当时因为我患了眼疾,看东西有困难,就由朱带头,詹殿后,我在中问,三人手拖手一起往上爬,几经辛苦爬到了顶,突然听到一声「土匪」,几个持枪的士兵似乎己在那里等待我们的出现,我们只好高举双手被押到东门城楼,因为负责人不在,只好等待。夜晚天凉,窗门又漏风,老鼠满地跑,那一个多钟头的等待真不是滋味。快到午夜时,主管大爷才手提军衣半醒半醉的哼调调回来,跟着就对我们审问,在得知一个是法院推事的女儿,一个是公路局段长的女儿,而我是邓家的四少爷后,就将我们释放。但那己过半夜一时后了。由于詹宝瑜家就在最近城楼的东门坡下,我们决定到她家过夜,谁知大门一开詹宝瑜只叫了一声「妈」就大哭起来,把她家人都弄得莫明其妙。后来由我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后,她家人才笑到人仰马翻,只是连声说你们这三个淘气鬼,活该。第二天我回到家中,家人既不知情,我就当甚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埋头便睡了。
另一事是在1945年初,正当考高中毕业试之前几个星期,我患上了伤寒。那是个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尤其在当时药物及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更加重了它的危险性。可说我又一次的幸运吧,在我们家附近住了一个军医学校姓朱的内科教授医生,在他的悉心诊治及护理下,加上当时家中经济情况可以在市面上买到英美出产最先进的药物,及各式各样的营养品,总算再一次从死神手中抢回了我的命,但亦不幸因病未能参加高中毕业试,令到我后来还要再读多一年高三。正在我病危的那几天,在学校运动会的会场中传出我病逝的消息,同学既不相信但又不敢来家中看我加以证实,因为伤寒是一种高度传染而又难以医治的病,所以只好在我家门口东张西望,看看是否确有其事。刚好那时我们家很不幸确有人过世,那是三哥的大女儿承惠,她长得非常漂亮,高挺的鼻梁,大大的眼睛,像一个洋娃娃,大概只有两岁吧,突然得了急病一两天就过世了。不用说当时一家人非常伤心。至今我仍忘不了当时我躺在病床上听见后厅钉棺材的锤声,加上女人们的哭喊声,令人伤心欲绝。可能市面上知道邓家有人死了,而我又刚好染上重症,就不免将此事联想到我的头上来。这段小插曲是我在事后才知道的。
因病未能参加毕业试而拿不到文凭考大学,不能不再读多一年高三。照理我可继续留在黔江,但我并没有留下而是跑去贵阳读省立贵阳高中。一来是我的同窗好友们毕业后都离开了安顺,不少还在贵阳工作或读大学,二来我不想同低我一班的同学们在一起,就趁此机会换一个环境。贵阳高中就在南明河畔的甲秀楼,今已成为贵阳重要风景点之一。当时我就住在学校附近若符大哥家,那是一座由留学德国回来的廷法二哥所设计欧陆式的洋房,外浅色配以墨绿色的门窗,非常好看及和谐。若符大哥一家住楼上,浲光四哥一家住楼下。当时伯符大哥的女儿惠芳惠珍亦在贵阳读女中,有一段时期亦住在若符哥处,加上承武一共四个青年人在一起很熟。虽然我是他们三人的长辈,但由于年龄相近,没有辈份的感觉,经常在一起做功课,看电影,游玩吃馆子等。
性格使然,亦如继往,在我就读贵阳高中的一年,仍是非常活跃。参加各种校内及校外的活动,组织歌咏团并担任团长,参加青年会的诗歌班,并跟一个出名的青年音乐家草田学唱歌。功课方面因为是重读,没有多大压力,轻易的考到了一张高中毕业文凭。虽然在贵阳只住了一年,但生活多姿多采,非常丰满,因此而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
1946年高中毕业后,我准备离家到上海考大学。起程前,廷琨二嫂收到了长沙(湖南省省会)来的急电告知她父亲病危要她立即前往。正好我去上海会路经长沙,所以就由我护送她及侄儿承维前往。当时我还把自己当在唱演《关公送嫂》呢!早行夜宿三日后终于到了长沙。但已赶不上见最后的一面,因为在我们抵达时已听到哭声震天了。在二嫂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去找当时驻在长沙的廷璞五哥,他带我玩了一两天就送我上火车去汉口,由于抗日胜利后由内地回去沿海地区的人数多,由武汉到上海的船票很难买到,好不容易买了到南京的。虽然不能到上海,但已很接近,到时就可乘火车前往。上了船才知连统舱都没有床位,只好打地铺睡在露天甲板上。幸好几天都没有下雨,而在熬过了三天两夜后,终于到了南京,再转乘火车到了上海。廷琨二哥当时在天津九十四军牟廷芳部下做野战医院院长,我就住在他空下来的房子。这是间两层高的楼房,他住在楼下,他的同学许姓牙医夫妇住在楼上,他俩对我很好,经常要我上楼一起吃饭,因为我身体不好,还定期为我注射针及葡萄糖钙。二哥住所安排得井井有条,衣物用品都很讲究,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和中」在虹口区天瞳路已开设了分公司,我就是到那里支取每月的生活费。
在上海四个月的这段日子,虽然只是我一个人,但生活并不寂寞,而且过得很有规律兼多姿多采。每天早上看两份很有份量的报纸,申报及大公报,使我这一生养成报不离手的习惯。下午温习考大学的功课或写写信。除上述许医生夫妇外,二嫂拜托了她的亲戚刘老伯夫妇照顾我,因此亦常到他们家吃饭,他们有一个未出嫁的女儿叫刘克洵弹得一手好钢琴,并喜爱文学及艺术,经常陪同我去听音乐看电影、话剧、舞蹈的演出等。电影有佐拉传、翠堤春晓、居礼夫人、国魂及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话剧如钗头凤、棠棣之花及日出。舞蹈则是由著名漫画家叶浅予的太太名舞蹈家戴爱莲所演出的边疆舞,当时来说很新鲜,真正是大开眼界。凑巧父亲的好友刘汉珍军长被派到上海参与接收工作(日本投降后需要去接收日本人及汉奸留下的工作及财物。)他家住在上海最高贵的住宅区愚园路,我常去作客,交际舞亦是在那时开始学的。为了满足好奇心,我还到附近的电影厂参观拍电影。考浙江大学时还顺便游览了西湖,考海军军官学校时到过南京,看了几个黔江的同学,大侄女惠芳的前度男朋友孙坚白还请了一天假陪我去游中山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