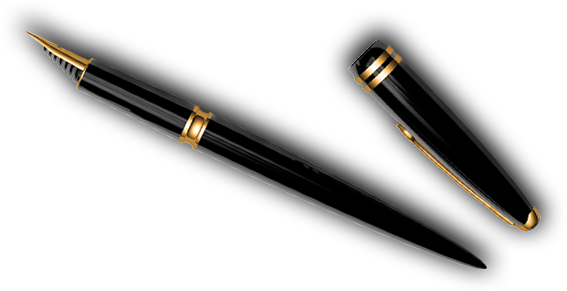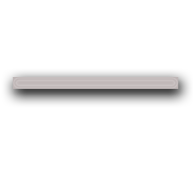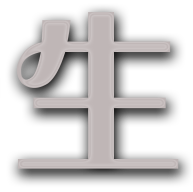我的成長 - 2
雖然上海給日本佔領但英法租界仍是安全區,匯錢並不困難,直到日本同英美開戰將英美法租界佔領後,匯錢才成了問題,母親為此事擔心不已,但父親叫母親不用操心,他認為廷琨自會有辦法解決的。父親果然說對了,據後來廷琨二哥說當時他是靠買賣二手照相機維生的,不只賺到錢並對相機有更深認識,而且對攝影亦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在滬期間他還繼續追隨一個俄國音樂家學習小提琴。我們可以想像新婚的廷琨拉小提琴而恩信用鋼琴伴奏,正所謂夫唱婦隨其樂也融融,多麼的羅曼蒂克,這亦可將當時的惡劣環境沖淡些吧。
廷琪三哥考取了貴州省立工學院的土木工程系後,就繼續他在上海復旦大學未完成的學業。學校是貴陽南郊十幾公里的圖雲關,我有時趁週末由安順跑去看他而他亦常回安順。正如前文所說雖然我們年齡有差距,但相處得非常好,常常睡在一張床上交談到半夜。他的愛好是多方面的。人聰明,手更巧。能將他的一條西裝褲改成一件夾克給我穿,自己沖洗照片,用鉛水在自製的模子裡製造鳥槍所用比火柴頭大一點的子彈。能為京劇或話劇的演員化裝,拉京胡,拉鋸琴,吹口琴,唱京戲,演話劇所謂無所不能,我對他是既崇拜又敬愛。在貴陽有一次我們同睡一床,聽到他半夜辛苦的咳嗽聲,令我感到難過及心痛,我求天主讓我代他病,代他咳嗽,別讓他那麼辛苦。在他想娶秀珍為妻時為父親反對,一來她母親是個寡婦,那就表示命不好,二來她家開的是棺材鋪,是一種厭惡性及不吉利的行業。三哥為此非常不開心,把自己關在樓上的睡房中兩天不下樓吃飯,我卻緊張得不得了,擔心他生病,又怕他會自殺,除了每天幾次在他睡房門口張望,又向天主祈禱,保佑三哥不要因此而生病,並能完成心願,母親亦從旁開解父親。由於三哥的果斷行動,讓父親看出了他的決心,加上母親及親友的說項,父親終於應允了這件婚事,至於我的祈禱是否有助,那就不得而知了。但他們終於結了婚,而當時在安順還是一件大事呢!
在黔江中學讀書時有兩件令人難忘的事值得在此一提:某一個暑假前夕在舉行了散學晚會後大約九點左右,我同朱亦蘭、詹寶瑜決定當晚不留在學校而回安順縣城。漆黑的夜空到處麟火閃閃,蟲聲閣閣,我們沿公路步行了一個多小時抵達了已關閉的城門,我們便喊城說是學生,但守城的軍人說甚麼都不肯開城門。如果再回學校又得再走一個鐘頭,而大家都很疲倦,正不知如何是好時,朱亦蘭記起在離城門兩百碼左右,有一處倒塌的城牆,我們決定就從那裡神不知鬼不覺的爬上去。當時因為我患了眼疾,看東西有困難,就由朱帶頭,詹殿後,我在中問,三人手拖手一起往上爬,幾經辛苦爬到了頂,突然聽到一聲「土匪」,幾個持槍的士兵似乎己在那裡等待我們的出現,我們只好高舉雙手被押到東門城樓,因為負責人不在,只好等待。夜晚天涼,窗門又漏風,老鼠滿地跑,那一個多鐘頭的等待真不是滋味。快到午夜時,主管大爺才手提軍衣半醒半醉的哼調調回來,跟著就對我們審問,在得知一個是法院推事的女兒,一個是公路局段長的女兒,而我是鄧家的四少爺後,就將我們釋放。但那己過半夜一時後了。由於詹寶瑜家就在最近城樓的東門坡下,我們決定到她家過夜,誰知大門一開詹寶瑜只叫了一聲「媽」就大哭起來,把她家人都弄得莫明其妙。後來由我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後,她家人才笑到人仰馬翻,只是連聲說你們這三個淘氣鬼,活該。第二天我回到家中,家人既不知情,我就當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埋頭便睡了。
另一事是在1945年初,正當考高中畢業試之前幾個星期,我患上了傷寒。那是個死亡率極高的傳染病,尤其在當時藥物及物資極度缺乏的情況下,更加重了它的危險性。可說我又一次的幸運吧,在我們家附近住了一個軍醫學校姓朱的內科教授醫生,在他的悉心診治及護理下,加上當時家中經濟情況可以在市面上買到英美出產最先進的藥物,及各式各樣的營養品,總算再一次從死神手中搶回了我的命,但亦不幸因病未能參加高中畢業試,令到我後來還要再讀多一年高三。正在我病危的那幾天,在學校運動會的會場中傳出我病逝的消息,同學既不相信但又不敢來家中看我加以証實,因為傷寒是一種高度傳染而又難以醫治的病,所以只好在我家門口東張西望,看看是否確有其事。剛好那時我們家很不幸確有人過世,那是三哥的大女兒承惠,她長得非常漂亮,高挺的鼻樑,大大的眼睛,像一個洋娃娃,大概只有兩歲吧,突然得了急病一兩天就過世了。不用說當時一家人非常傷心。至今我仍忘不了當時我躺在病床上聽見後廳釘棺材的鎚聲,加上女人們的哭喊聲,令人傷心欲絕。可能市面上知道鄧家有人死了,而我又剛好染上重症,就不免將此事聯想到我的頭上來。這段小插曲是我在事後才知道的。
因病未能參加畢業試而拿不到文憑考大學,不能不再讀多一年高三。照理我可繼續留在黔江,但我並沒有留下而是跑去貴陽讀省立貴陽高中。一來是我的同窗好友們畢業後都離開了安順,不少還在貴陽工作或讀大學,二來我不想同低我一班的同學們在一起,就趁此機會換一個環境。貴陽高中就在南明河畔的甲秀樓,今已成為貴陽重要風景點之一。當時我就住在學校附近若符大哥家,那是一座由留學德國回來的廷法二哥所設計歐陸式的洋房,外淺色配以墨綠色的門窗,非常好看及和諧。若符大哥一家住樓上,浲光四哥一家住樓下。當時伯符大哥的女兒惠芳惠珍亦在貴陽讀女中,有一段時期亦住在若符哥處,加上承武一共四個青年人在一起很熟。雖然我是他們三人的長輩,但由於年齡相近,沒有輩份的感覺,經常在一起做功課,看電影,遊玩吃館子等。
性格使然,亦如繼往,在我就讀貴陽高中的一年,仍是非常活躍。參加各種校內及校外的活動,組織歌詠團並擔任團長,參加青年會的詩歌班,並跟一個出名的青年音樂家草田學唱歌。功課方面因為是重讀,沒有多大壓力,輕易的考到了一張高中畢業文憑。雖然在貴陽只住了一年,但生活多姿多采,非常豐滿,因此而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
1946年高中畢業後,我準備離家到上海考大學。起程前,廷琨二嫂收到了長沙(湖南省省會)來的急電告知她父親病危要她立即前往。正好我去上海會路經長沙,所以就由我護送她及侄兒承維前往。當時我還把自己當在唱演《關公送嫂》呢!早行夜宿三日後終於到了長沙。但已趕不上見最後的一面,因為在我們抵達時已聽到哭聲震天了。在二嫂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去找當時駐在長沙的廷璞五哥,他帶我玩了一兩天就送我上火車去漢口,由於抗日勝利後由內地回去沿海地區的人數多,由武漢到上海的船票很難買到,好不容易買了到南京的。雖然不能到上海,但已很接近,到時就可乘火車前往。上了船才知連統艙都沒有床位,只好打地舖睡在露天甲板上。幸好幾天都沒有下雨,而在熬過了三天兩夜後,終於到了南京,再轉乘火車到了上海。廷琨二哥當時在天津九十四軍牟廷芳部下做野戰醫院院長,我就住在他空下來的房子。這是間兩層高的樓房,他住在樓下,他的同學許姓牙醫夫婦住在樓上,他倆對我很好,經常要我上樓一起吃飯,因為我身體不好,還定期為我注射針及葡萄糖鈣。二哥住所安排得井井有條,衣物用品都很講究,是一個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和中」在虹口區天瞳路已開設了分公司,我就是到那裡支取每月的生活費。
在上海四個月的這段日子,雖然只是我一個人,但生活並不寂寞,而且過得很有規律兼多姿多采。每天早上看兩份很有份量的報紙,申報及大公報,使我這一生養成報不離手的習慣。下午溫習考大學的功課或寫寫信。除上述許醫生夫婦外,二嫂拜託了她的親戚劉老伯夫婦照顧我,因此亦常到他們家吃飯,他們有一個未出嫁的女兒叫劉克洵彈得一手好鋼琴,並喜愛文學及藝術,經常陪同我去聽音樂看電影、話劇、舞蹈的演出等。電影有左拉傳、翠堤春曉、居禮夫人、國魂及一江春水向東流等,話劇如釵頭鳳、棠棣之花及日出。舞蹈則是由著名漫畫家葉淺予的太太名舞蹈家戴愛蓮所演出的邊疆舞,當時來說很新鮮,真正是大開眼界。湊巧父親的好友劉漢珍軍長被派到上海參與接收工作(日本投降後需要去接收日本人及漢奸留下的工作及財物。)他家住在上海最高貴的住宅區愚園路,我常去作客,交際舞亦是在那時開始學的。為了滿足好奇心,我還到附近的電影廠參觀拍電影。考浙江大學時還順便遊覽了西湖,考海軍軍官學校時到過南京,看了幾個黔江的同學,大侄女惠芳的前度男朋友孫堅白還請了一天假陪我去游中山陵。